2021-04-07 09:5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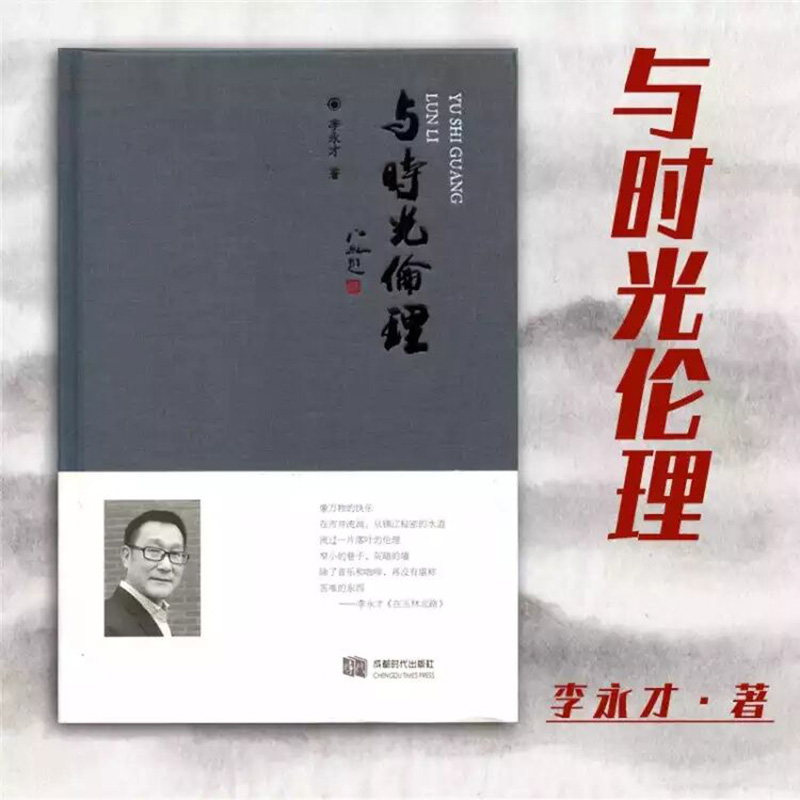
何光顺(广东)
谁在托付?托付何物?托付与谁?
李永才《与时光伦理》第三辑《布列瑟农的下午》是以《托付之物》开篇的。“我人生的宅基地,该种的草木/都种过了。紫藤、葡萄、鱼腥草/春华秋实,都是季节之物/不可托付终身/只有一棵黄葛树,或许会成为/我最后的依靠”,诗人在托付,托付他的生存和信仰,不是托付给何人,却是托付给了黄葛树。太多的季节之物的变化,都埋葬了转瞬即逝的生命印记,只有那一棵黄葛树成为了诗人精神的象征物,意味着永恒和信任。
诗人的作品,总是充满着追问,一种孤寂者无法相信这个世界的疑惑和彷徨,“如果桃花不销魂,流水的去向/该与谁言说?”(《阳光多么安详》),“谁能在这片时尚的空间/找到无私的想象?当葵花低头时/我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纯洁的光芒”(《小尾巴狗,或者黑科技》),一种不确定感,世界的不可把握性,让诗人难以找到对话者,但诗人并不悲观和消沉,他不仅把自我托付给黄葛树,而且他的心中始终隐藏着那样一个“你”。“我”与“你”的对话是直接的,是无须转述的,“你对每一粒酸甜,都深怀敬意”,“该有一个人,接近空寂的黄昏/为你送去一杯咖啡”(《阳光多么安详》)。“无知的早晨,/我不再关心鸟类的音乐会”“四合的宁静,让我音乐一样的耳朵/被潮湿的记忆唤醒”(《近乎圆形的想象力》),只有在摒弃喧嚣的宁静中,我将走向你。为你送去咖啡的人,也大约不过是另一个自己。
那一个“你”究竟是谁?他(她)或许与黄葛树一样值得信任,“一个人,坐进布列瑟农的下午/像钉在桌面的茶杯/沦陷于三月的深绿,忘乎所以”,这“一个人”,是谁?或者既是孤独寂静中的“我”,也是我所寻找的“你”,是双重的一。这“一个人”也是跨越了少年、青年、中年以及未来老年的那样的“我”或“你”,是岁月沧桑里的我和你不断交叉叠合的多重影像的一,“一个少年的春梦/是红在黄梁上的樱桃”,“剩下的光阴,将变得轻松”(《梦与樱桃何其相似》),诗人将流逝和瞻望都指向了那样“一个人”,那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你,是必须在存在与时间的维度上被反复诘问的自我又非我的矛盾,正如诗人所说的:“那些蔬菜和水果的交响/是自由的问候,是狡黠的时光/我无法置身事外”(《明亮的假日》),这问候里是自由,却更是爱,是生命的主宰,来自爱情,也来自神所恩赐,“世界有了光,但人间的光/比不过上帝的伟大”,诗人所说的上帝,不是某个宗教的上帝,而是心灵的上帝,“我丢掉了一些幻想:爱情/云朵和地上的黑芝麻”(《较场口的情绪》)。
“我”和“你”,是“一个人”,他会变幻出不同的形式,在虚拟的空间,也在现实的生活中存在,他是唯一的,是在诗人曾经难以信任的季节之物中以多重面相存在,却始终保持着唯一和自由,他在一切变幻之物中看到了心灵之神的纯粹和永恒,“一个信仰自然的人/绝不轻言放弃,任何一片枝叶/对高山流水的倾听”(《气象》),中国诗人的信仰,总是自己找到的。诗人写到了华夏民族历史上那些作为商业交易的各种流通凭证,诗人看到“天下万物,不过一张纸/如果选择它的正面/那么它的反面/就是你的一生,别无选择的/——机会成本”(《春秋大梦一张纸》)。“你的一生”也是“我的一生”,它有正面和反面,或者我和你就构成了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这张纸片,可以交换世间一切物,或比一切物都重,它就是一切物的价值。
“一个人”既是确定的,也是不确定的,它是“我”和“你”的同一,却又在变幻的季节里有不同的化身,“一个人走进三月的小雨/同那些喜形于色的事物,说些/不冷不热的闲话”(《三月的小雨》),“我”和“你”都得去经历淅沥的雨季,都得在阳光重来之前渡过潮湿和阴暗。但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必须去经历,去随四季轮回。
在第四辑《秋天的多样性》中,诗人要写中国人最敏感的秋天了。“‘万物惊秋’。一场秋雨/是否来自天意/而草野的谷禾,已不在乎这些了/只待一阵秋风/将漫山的枝叶,吹出秋意”(《立秋的意义》),它随生活起伏,“如风吹草长/越来越简单”(《风吹草长的日子》),“我”和“你”的关系,就在这季节的轮回中不断变化,“我要赞美江南的秋天/它比你的想象/更为辽远”,“在我的眼里/秋天是一位痴情的少女/从一片废墟走出”,“秋天是道德,是伦理/是一个虚怀若谷的哲人”(《秋天的经验》),秋天本身就意味着丰富的经历,它是经历了春天的初生、夏天的浓烈,而后才到达秋天的萧瑟,并将预示着冬天的枯寂。“一个人”的“秋天”,就意味着生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重维度的统一。
于是,诗人写秋天的多样性,就不只是在写自然的秋天,而是在写生命本身的苍凉,写“我”和“你”作为“一个人”的统一,“在另一个天地里/现实与浪漫的,每一次对话/都会产生不同寻常的错觉”(《与植物对话》),“我”是现实的?“你”是浪漫的?不断转换,不断呼唤、倾听和应答,从而确立新的“自我”?诗人必须学会观察和反思,就像心灵的苍穹和脚下的大地一样辽阔,可以容纳万类霜天竞自由,“据观察:秋天的确是这样/为了让大地,获得一丝凉意/不知制造了多少,飞短流长的声响”(《新观察》),诗人是象天法地者,在春与秋的轮回中,书写天地之象,那仰观俯察,早就在他纯粹的精神里预设了最完美的图案,而世界不过是他的精神的投影。
诗人李永才不断地书写季节、万物、气象,写到“我”和“你”在这变幻和流动中的随缘和坚持,不断去探问,其笔触的灵性和活泼,就如来自上天和造化的馈赠,他早就与荣枯的草木、潺潺的溪水合而为一,“树上的鸟儿,要与上帝对话/它们在谈论什么呢?/昨天的一场雨,让我播下的种子,有了生长的理由”(《识天气》),这对话,是在随时随处发生,不是鸟儿要与上帝对话,而是唯一的我领会了我的栖居与存在的关系。“我的天空隐于屋檐,作为回应/江南在下雪”(《旧事物》),我和你的对答,也是万物互见的交流,都要以我的屋檐或居所来容纳。“像悲伤的落日,被一阵秋风/吹向枯朽的屋檐/多少梦中的鸟影,醒来时/都找不到自己的主人”(《秋天是蝴蝶的外衣》),秋天,是诗人永才最关注的季节,那是一个经历了生命沧桑的诗人看到了时光和生命流逝中的丰富和复杂。
秋天在向世人道说,就像诗人向着万物说话,“被秋风解放的身体,透明/如一只橘色的野狼”,“你新生的发辫,是秋天的胡须/五彩斑斓地起伏/就像我手上的潮汐/涌上树枝是鸟,落在树下/就成了抽象的言辞”(《秋天的言辞》),秋天,意味着不再年少,也不再青春,它是人生的中年,它不再直接表露情感,它如秋叶寂然,却隐藏生命至深,它是抽象的玄意。诗人永才太爱秋了,在秋意里,他写出了“我”和“你”所可能的一切关系,那是细腻、辽阔、苍茫和高远,“有阳光的时候/你试图看见大海,看不见也不要紧/可以想象一只海贝”(《秋风过南湖》),“草堂的钥匙,早已被一江锦水/丢失在唐朝/你无需去寻找。穿过那一丛/被秋风撩乱的胡须/一样可以,沿着时间的伦理/走进一个诗人的苦难”(《草堂的钥匙》),永才笔下的“一个人”,是“我”和“你”相互应合所达至完整,是“一个诗人”的纯粹和唯一,他始终是一个“赶路人”,他在旅途上听见了一切,“在你的衣领,有鸟儿的暗语/有黎明的钟声/等你,一个年轻的天使/用一个小小的眼神/去把它敲响”(《第五个夜晚》),诗人永远是“一个人”,只有在他的诗篇里,才能实现“我”和“你”对话,他是木铎,振响时代的大音,呼唤所有人醒来,让每个人从稚嫩走向成熟!
一个人的诗篇,是与世界应和的诗篇,是融复调众声于唯一。一个始终在赶路的诗人,在“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里,宣告着秋天的消息,也是生命成熟的消息。
2021-04-07 09:5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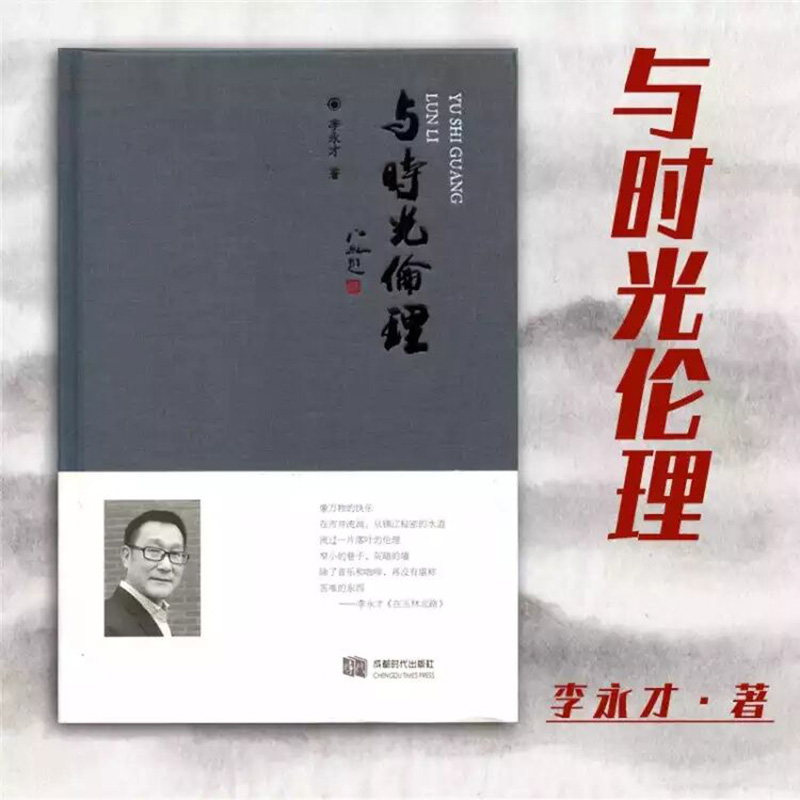
何光顺(广东)
谁在托付?托付何物?托付与谁?
李永才《与时光伦理》第三辑《布列瑟农的下午》是以《托付之物》开篇的。“我人生的宅基地,该种的草木/都种过了。紫藤、葡萄、鱼腥草/春华秋实,都是季节之物/不可托付终身/只有一棵黄葛树,或许会成为/我最后的依靠”,诗人在托付,托付他的生存和信仰,不是托付给何人,却是托付给了黄葛树。太多的季节之物的变化,都埋葬了转瞬即逝的生命印记,只有那一棵黄葛树成为了诗人精神的象征物,意味着永恒和信任。
诗人的作品,总是充满着追问,一种孤寂者无法相信这个世界的疑惑和彷徨,“如果桃花不销魂,流水的去向/该与谁言说?”(《阳光多么安详》),“谁能在这片时尚的空间/找到无私的想象?当葵花低头时/我的眼里,突然闪过/一丝纯洁的光芒”(《小尾巴狗,或者黑科技》),一种不确定感,世界的不可把握性,让诗人难以找到对话者,但诗人并不悲观和消沉,他不仅把自我托付给黄葛树,而且他的心中始终隐藏着那样一个“你”。“我”与“你”的对话是直接的,是无须转述的,“你对每一粒酸甜,都深怀敬意”,“该有一个人,接近空寂的黄昏/为你送去一杯咖啡”(《阳光多么安详》)。“无知的早晨,/我不再关心鸟类的音乐会”“四合的宁静,让我音乐一样的耳朵/被潮湿的记忆唤醒”(《近乎圆形的想象力》),只有在摒弃喧嚣的宁静中,我将走向你。为你送去咖啡的人,也大约不过是另一个自己。
那一个“你”究竟是谁?他(她)或许与黄葛树一样值得信任,“一个人,坐进布列瑟农的下午/像钉在桌面的茶杯/沦陷于三月的深绿,忘乎所以”,这“一个人”,是谁?或者既是孤独寂静中的“我”,也是我所寻找的“你”,是双重的一。这“一个人”也是跨越了少年、青年、中年以及未来老年的那样的“我”或“你”,是岁月沧桑里的我和你不断交叉叠合的多重影像的一,“一个少年的春梦/是红在黄梁上的樱桃”,“剩下的光阴,将变得轻松”(《梦与樱桃何其相似》),诗人将流逝和瞻望都指向了那样“一个人”,那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你,是必须在存在与时间的维度上被反复诘问的自我又非我的矛盾,正如诗人所说的:“那些蔬菜和水果的交响/是自由的问候,是狡黠的时光/我无法置身事外”(《明亮的假日》),这问候里是自由,却更是爱,是生命的主宰,来自爱情,也来自神所恩赐,“世界有了光,但人间的光/比不过上帝的伟大”,诗人所说的上帝,不是某个宗教的上帝,而是心灵的上帝,“我丢掉了一些幻想:爱情/云朵和地上的黑芝麻”(《较场口的情绪》)。
“我”和“你”,是“一个人”,他会变幻出不同的形式,在虚拟的空间,也在现实的生活中存在,他是唯一的,是在诗人曾经难以信任的季节之物中以多重面相存在,却始终保持着唯一和自由,他在一切变幻之物中看到了心灵之神的纯粹和永恒,“一个信仰自然的人/绝不轻言放弃,任何一片枝叶/对高山流水的倾听”(《气象》),中国诗人的信仰,总是自己找到的。诗人写到了华夏民族历史上那些作为商业交易的各种流通凭证,诗人看到“天下万物,不过一张纸/如果选择它的正面/那么它的反面/就是你的一生,别无选择的/——机会成本”(《春秋大梦一张纸》)。“你的一生”也是“我的一生”,它有正面和反面,或者我和你就构成了一张纸的正面和反面,这张纸片,可以交换世间一切物,或比一切物都重,它就是一切物的价值。
“一个人”既是确定的,也是不确定的,它是“我”和“你”的同一,却又在变幻的季节里有不同的化身,“一个人走进三月的小雨/同那些喜形于色的事物,说些/不冷不热的闲话”(《三月的小雨》),“我”和“你”都得去经历淅沥的雨季,都得在阳光重来之前渡过潮湿和阴暗。但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他必须去经历,去随四季轮回。
在第四辑《秋天的多样性》中,诗人要写中国人最敏感的秋天了。“‘万物惊秋’。一场秋雨/是否来自天意/而草野的谷禾,已不在乎这些了/只待一阵秋风/将漫山的枝叶,吹出秋意”(《立秋的意义》),它随生活起伏,“如风吹草长/越来越简单”(《风吹草长的日子》),“我”和“你”的关系,就在这季节的轮回中不断变化,“我要赞美江南的秋天/它比你的想象/更为辽远”,“在我的眼里/秋天是一位痴情的少女/从一片废墟走出”,“秋天是道德,是伦理/是一个虚怀若谷的哲人”(《秋天的经验》),秋天本身就意味着丰富的经历,它是经历了春天的初生、夏天的浓烈,而后才到达秋天的萧瑟,并将预示着冬天的枯寂。“一个人”的“秋天”,就意味着生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重维度的统一。
于是,诗人写秋天的多样性,就不只是在写自然的秋天,而是在写生命本身的苍凉,写“我”和“你”作为“一个人”的统一,“在另一个天地里/现实与浪漫的,每一次对话/都会产生不同寻常的错觉”(《与植物对话》),“我”是现实的?“你”是浪漫的?不断转换,不断呼唤、倾听和应答,从而确立新的“自我”?诗人必须学会观察和反思,就像心灵的苍穹和脚下的大地一样辽阔,可以容纳万类霜天竞自由,“据观察:秋天的确是这样/为了让大地,获得一丝凉意/不知制造了多少,飞短流长的声响”(《新观察》),诗人是象天法地者,在春与秋的轮回中,书写天地之象,那仰观俯察,早就在他纯粹的精神里预设了最完美的图案,而世界不过是他的精神的投影。
诗人李永才不断地书写季节、万物、气象,写到“我”和“你”在这变幻和流动中的随缘和坚持,不断去探问,其笔触的灵性和活泼,就如来自上天和造化的馈赠,他早就与荣枯的草木、潺潺的溪水合而为一,“树上的鸟儿,要与上帝对话/它们在谈论什么呢?/昨天的一场雨,让我播下的种子,有了生长的理由”(《识天气》),这对话,是在随时随处发生,不是鸟儿要与上帝对话,而是唯一的我领会了我的栖居与存在的关系。“我的天空隐于屋檐,作为回应/江南在下雪”(《旧事物》),我和你的对答,也是万物互见的交流,都要以我的屋檐或居所来容纳。“像悲伤的落日,被一阵秋风/吹向枯朽的屋檐/多少梦中的鸟影,醒来时/都找不到自己的主人”(《秋天是蝴蝶的外衣》),秋天,是诗人永才最关注的季节,那是一个经历了生命沧桑的诗人看到了时光和生命流逝中的丰富和复杂。
秋天在向世人道说,就像诗人向着万物说话,“被秋风解放的身体,透明/如一只橘色的野狼”,“你新生的发辫,是秋天的胡须/五彩斑斓地起伏/就像我手上的潮汐/涌上树枝是鸟,落在树下/就成了抽象的言辞”(《秋天的言辞》),秋天,意味着不再年少,也不再青春,它是人生的中年,它不再直接表露情感,它如秋叶寂然,却隐藏生命至深,它是抽象的玄意。诗人永才太爱秋了,在秋意里,他写出了“我”和“你”所可能的一切关系,那是细腻、辽阔、苍茫和高远,“有阳光的时候/你试图看见大海,看不见也不要紧/可以想象一只海贝”(《秋风过南湖》),“草堂的钥匙,早已被一江锦水/丢失在唐朝/你无需去寻找。穿过那一丛/被秋风撩乱的胡须/一样可以,沿着时间的伦理/走进一个诗人的苦难”(《草堂的钥匙》),永才笔下的“一个人”,是“我”和“你”相互应合所达至完整,是“一个诗人”的纯粹和唯一,他始终是一个“赶路人”,他在旅途上听见了一切,“在你的衣领,有鸟儿的暗语/有黎明的钟声/等你,一个年轻的天使/用一个小小的眼神/去把它敲响”(《第五个夜晚》),诗人永远是“一个人”,只有在他的诗篇里,才能实现“我”和“你”对话,他是木铎,振响时代的大音,呼唤所有人醒来,让每个人从稚嫩走向成熟!
一个人的诗篇,是与世界应和的诗篇,是融复调众声于唯一。一个始终在赶路的诗人,在“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里,宣告着秋天的消息,也是生命成熟的消息。